作者:刘亚敏
在江南。在咸宁。在通城县四庄乡。在国家级湿地公园。一个大自然的土著家庭在这里和睦地生活着——


我是在穿过一栋栋钢筋混凝土楼盘和一片片平畴、丘冈后,与他们拥抱的。
他们住在水洼之中,用黄色的土壤与水面保持近二米的距离,像相机镜头上一个金色的环。他们不喜欢声音,很少发现路和人居的房子。
从船上望去,树木的家像紧闭上门帘的绿色蒙古包,是不能随便进入的。但当我靠近他们,树干和树干渐渐松开。他们谨慎地欢迎我。我可以休息、乘凉。但我猜测,他们正监视着我,并心存戒备。
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,年纪最大的住在中间,而那些小家伙,有的还刚刚长出嫩芽,差不多遍地都是。
他们的死亡是缓慢而悄无声息的。他们让死去的树也站立着,直至腐朽而变成尘埃。
他们用长长的手臂相互抚摸,像盲人凭此确信他们全都在那里。如果风气喘吁吁要将他们连根拔起,他们的手臂就愤怒地挥动。但是,在他们彼此之间,只有和睦的低语而无任何争吵。
我感到这才是我真正的家。这些树木迟早会接纳我。而为了配受这个光荣,我学习应该懂得的事情:懂得眼观天色,监视流云;懂得呆在原地一动不动;懂得而且几乎学会了沉默!


她们是从树木家中派生和分离出来的。她们视树木为自己的族兄。她们并没有离开多远,只是在树木的旁边另立门户。
她们喜欢笑,敞开心扉的笑。在树林中不起眼,就手牵着手,站在每一条进山的小路边来笑。每一朵花,都像小姑娘的酒窝;都像迎接舅舅的小外甥女。
花的家是个女儿国。牡丹是国王,向日葵是皇太后,玫瑰、月季、杜鹃、山茶是公主,牵牛花是驸马,总有点纠缠不休。这里艳丽、妩媚、温柔、平静、滋润,让进来了的人都不想离开。
蝴蝶来探亲,显得有点轻佻和得意。而花们的表情看上去非常淡定。只有蜜蜂是她们公开的情人。她们乐意让蜜蜂把木房子一排排搭建在自己的后院,天天耳鬓厮磨,卿卿我我,直至脱尽花衣。
花朵的家庭人气旺盛,枝繁叶茂时,每个人的脸蛋都依偎在一起,分不清你我。花朵的凋谢是悄无声息的,总带着雨水和风韵。铅华过后,她们的逝去,都是为了殉情。
我感到我是个花痴。见一种花爱一种花,连自己的名字也女性化了。而且我开始珍惜时光,学会打扮,非常关心自己的容颜,学会了该含蓄时含蓄,该表现时表现,并且懂得幸福的感受是——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!


白鹭、云雀、凤尾雉、鸳鸯、燕子、布谷、白头翁、啄木鸟们是大溪的歌手和山水诗人。他们聚会时,树木和花草都显得温文尔雅。他们在丛林间栖息时,就是树木的花朵;他们在天空中飞翔时,就是溪流的音符。
他们把赛诗台搭在溪边,把演唱会的时间安排在早晨空气质量最好的时候。他们围绕着一个保护地球村的共同主题,你方唱罢我登场,尽情展示着歌喉。
作为培养后代的摇篮,他们把家安在树木的隐蔽之处。从孵化梦想开始,就注重培养孩子们的音乐天赋,要求他们学会聆听和共鸣,而且要学会进入“我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
他们天生机警和胆怯,听惯了风声却害怕爆响,总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有时他们看你,眼睛里总带着猜测。看得出来,这是善意的,也是交流、对话的开端。
借宿在纸棚村,我彻夜听见那只守时的杜鹃在不断呼唤: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!”


在大溪,带着澄明的心欣赏那些水中的精灵,他们就不是与熊掌相提并论的“我所欲也”。
他们在自己的水域里生活,鲢鱼是鲢鱼一层,草鱼是草鱼一层,青鱼是青鱼一层,银鱼是银鱼一层。他们友好相邻,从不相互攻击。而那些鱼鳅、乌龟、鳖,却总爱在黝黑的泥泞里与甜藕和荷花为伴,还在泥水的表面留下许多五花八门的路径。那些残荷书写的象形字,也许正是他们吐露的心声。
溪水在欢快地流淌着,“歪嘴白”总爱带着他的团队在清晨或者山雨过后溯水而上。他们在溪水中游弋,像看得见的电流,有时一线线分开,有时又合成一股,还在每一个“接触不良”的缺口拼命击起“噼啪”作响的浪花,将那泉水的歌儿升上高潮。
偌大的水面供鱼儿生存,不知谁的资历最老。有人在太阳伞下来守候和诱捕他们,但总是那些涉世不深的小东西容易上钩。每次见那些小小的鱼儿在钓线和网线上活蹦乱跳,我总心怀怜悯。
当蓝天、白云映照在湖水里,水天成为一体,我的心豁然开朗。鱼儿在其间往来穿梭,宛如在梦幻与现实、仙界与凡尘、远古与未来间反复涉猎。我忽然感觉到鱼儿是有禅意的,特别是那尾滑溜溜的大嘴鳙。
在大溪的水里,我打碎了自己的影子之外,捞起了一句湿漉漉的古训:“平生最爱鱼无舌,游遍江湖少是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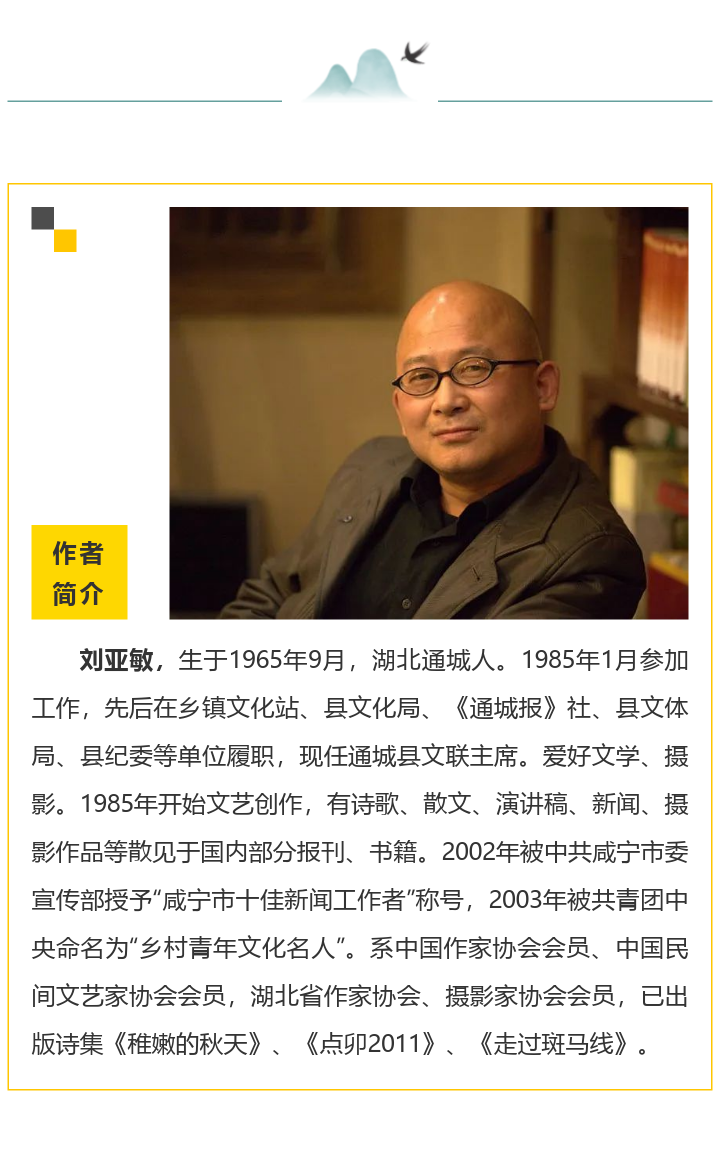
图文编辑:吴滟|责任编辑:胡颖|审核:傅凡
监制:黎雄



